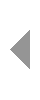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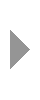



(2019年11月)鉛筆能擦掉,油畫能蓋過,水墨下了筆就不能回頭。或許,很多人會認為水墨藝術很難拿捏,是大師經過多年時間的沉澱才能駕馭。但對大學時期才真正研究水墨藝術的新晉藝術家劉敬楠(L8-10)來說卻不是如此。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他,不但以水墨檢視人與社會,更肩負起以藝術影響新一代的願景。
流暢貫通,是他沉醉水墨的原因;舉重若輕,他輕輕以水墨帶過沉重的話題;黑白分明,他由沉默的觀察者蛻變為社會的發聲者。
J:JCCAC
L:劉敬楠
J:為甚麼會選擇修讀藝術?
L:年少時,我是一個沒有自信的小伙子,總是活在與我就讀同一所中學,成績名列前茅的姊姊的影子之下。當時的我只喜歡在課本上畫公仔,卻獲得視覺藝術科老師的鼓勵,這位老師因此啟蒙了我,讓我從藝術創作中建立自信,找到自己的價值。
我記得這位老師曾經帶我們到菜園村的示威現場作考察。老師告訴我們藝術並不只是憑空幻想,而是要張開眼睛觀察社會,將吸收到的事物化作日後創作的養分。我的藝術種子大概就是從那時埋下了。老師的身教,讓我了解到藝術教育對擴闊視野,以及文化傳承的重要性。因此,現在的我除了創作,也有兼職教畫,希望以藝術影響生命。
藝術最有趣的地方是它能跨學科,並連繫不同的人。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教授工筆的工作坊中有學生問我:「鉛筆和工筆畫出來的線條有甚麼分別?」這引發我去反思媒介的定義—— 從前只有毛筆,國畫自然是圍繞毛筆的一套系統,但到了當代,國畫是否就一定要用毛筆去畫?其實鉛筆代替工筆勾線,再用國畫顏料上色也是可以的。當然,我們首先要掌握各種素材並消化當中的學術知識,再化繁為簡或突破框框——這就是藝術教育。
J:水墨於你的吸引之處是⋯⋯
L:中學時期其實我並不喜歡水墨,但後來大學導師讓我明白到水墨原來充滿不同的可能性及面向,既可以黑白單一,也可以色彩繽紛,更能貫通其他媒介,例如西方水彩及版畫的技法與水墨類同,水墨的材料像墨硯及工筆亦各有規律和特色,理解媒介特性並使之相互溝通,其中無盡的可能性令我著迷。
雖然我的年資尚淺,在教班的時候偶被質疑,但我認為水墨並不只是大師的玩意或只可以跟隨傳統,新水墨也可有其演繹方法,能為水墨帶來新視野及變化,例如我曾嘗試以水墨畫動畫。
J:你為何鐘情日本文學的「無賴派」,又如何把它融入到你的創作之中?
L:我曾因家庭狀況、畢業後的工作壓力等問題而感憂鬱,因此當讀到「無賴派」作家太宰治的書時特別有共鳴,更選擇以這種頹喪、扭曲及鬼怪的風格入畫,以釋放負面情緒。
初時,我的畫作全都是黑白的。其後,放下工作,重新教小朋友畫畫,我才發現色彩於水墨也有其可取之處,現在亦懂得運用顏色去平衡陰暗的題材及自己的心理,是藝術「自」療的一種。
我是一個喜歡分析及讀歷史的人,因此對於藝術,我會先看文字,再看畫面。除了文學,我也會借鑑浮世繪。至於創作素材,比起紙,木板更具重量,而且毛筆觸碰表面時的摩擦力大,適合用以表現沉重的氛圍。
J:是甚麼令你想要探討人與社會的病態關係?你如何看待現今的香港社會?
L:可能因為我從小便接觸大大小小的社會事件,長大後就能體會社會存在著許多的不公義及壓迫,情緒會被牽動,繼而激發我以病態社會的角度去創作。這也是為甚麼我的作品從來沒有展示「美好」的一面。有沒有人欣賞是其次,始終自己是作品的第一個觀眾,能否抒發自身感受才是最重要。
以前,政治不會找上門,現在卻是不能迴避。社會上紛爭不斷,我想是因為存在著不公及深層次問題。社會普遍對事不對人,但這卻似乎忽略了「人」,也是為何大家對近日的事態都容易變得敏感,撕裂愈是嚴重。我喜歡透過觀察人來洞悉社會,例如人的表情往往反映社會氣候,所以你會發現近來很多人「黑口黑面」。
我認為香港人上街表達訴求,是希望為下一代爭取一個相對民主、自由和公平的社會。「兄弟爬山,各自努力」,不同崗位的人可各自發揮其影響力,所以我想我還是應繼續專心畫畫。
J:可以告訴我們更多關於你將在元創方舉行之展覽「在地游走」嗎?
L:是次展覽也是以病態社會為題,參考文學作品《對倒》的雙線記敍,透過發聲者和沉默者的角度,直述和暗示的方法,描繪香港社會狀況及生活上荒謬的事情。一直以來,我的作品都較常描述人們被社會蠶食。但現在情況有所不同,而這種改變值得被記錄。
J:作為年輕藝術家,在創作以外也有「正職」,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?
L:我的身份比較特殊,正職是在公營機構從事藝術行政,剩下的時間就是教畫及創作。把薪金及餘暇投放到藝術,有人問我值得嗎?從經濟的角度看可能是沒有回報,但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要以物質去計算,能經營及投資於自己的興趣,在當中獲得的滿足感是無價的。教畫雖然辛苦,但能透過分享我的知識,讓學生們擁有審美能力,多一種方式表達自己,這對藝術家及藝術界長遠來說都是一件好事。所以說,工作、創作、教畫及遊行,暫時在我生命裡都是缺一不可的。
下載《JCCAC節目表》2019年11月號,按此
更多「藝述心言」文章,按此




